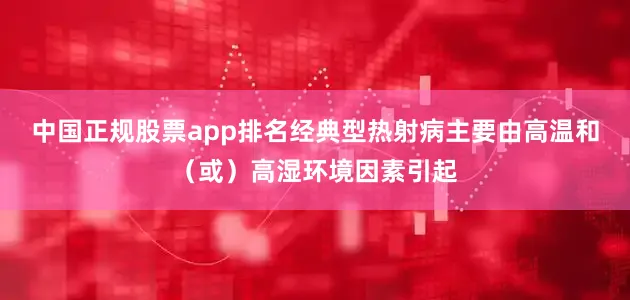乳腺癌是全球女性癌症死亡的首要原因,迫切需要低副作用疗法。基于肽的治疗策略因其安全性和功能可调性成为有前景的方向。肽基靶向载体可特异性结合癌细胞过表达受体,提高药物精准性。细胞穿透肽(CPPs)则通过增强细胞膜穿透克服低内吞问题。基于肽的疫苗发展迅速,目前有13种主要乳腺癌肽疫苗处于各期临床试验。此外,抗癌肽药物已用于临床,其中新型肽能逆转乳腺癌耐药性。本综述重点聚焦这些肽基策略(靶向载体、CPP、肽疫苗、抗癌肽)在乳腺癌治疗和预防中的研究进展。
1、介绍
癌症是全球主要死因,2020年造成超995万人死亡(GLOBOCAN数据)。在女性中,乳腺癌是最常见的癌症类型(IARC数据),也是癌症相关死亡的第二大主因。美国2020年约有279,110例新发乳腺癌病例(Siegel等数据)。转移性乳腺癌的5年生存率极低,仅为22%。乳腺癌主要分为三种亚型:最常见的激素受体阳性型(60%-70%)、三阴性型(TNBC,15%-20%)和HER2阳性型。早期诊断和适当治疗对改善乳腺癌预后至关重要。
展开剩余96%乳腺癌的传统治疗方法包括靶向治疗、放射治疗、化疗、手术和激素治疗,常依据亚型单独或联合使用。化疗是当前治疗的基石,未来仍将发挥核心作用。然而,化疗药物常引发严重副作用和耐药性。克服毒副作用和耐药性是未来研究的主要目标。
多肽因其可大规模生产、安全性和功能可调性,在递送各类抗癌药物中至关重要。中性电荷多肽系统含有一个阳离子肽(如胍基功能化的聚(L-赖氨酸))和pH敏感肽聚合物嵌段(如聚乙二醇-b-聚(L-赖氨酸)接枝环己烯-1,2-二羧酸酐)。这最终赋予整个结构中性电荷。值得注意的是,该中性电荷肽系统在体外对耐药细胞(MCF-7/ADR)和非耐药细胞(MCF-7)具有相似的抗肿瘤效果。更重要的是,这种中性电荷特性有效规避传统阳离子抗癌药物常见的体内不稳定性和系统性毒性问题,显示出更好的安全性前景。苯丙氨酸二肽(FF)展现出独特的浓度依赖性自组装行为。在较低浓度(<7mg/mL)下,FF二肽通过分子间的π-π堆积相互作用,主要形成囊泡结构。而当浓度升高至>10mg/mL时,相同的π-π堆积作用则驱动其组装成纳米管结构。Wang等人合成聚乙二醇修饰的RAFF(PEG-RAFF)自主装纳米球用于siRNA的有效递送。在HER2胞外域,抗原肽CH401(YQDTILWKDIFHKNNQLALT)有效激活CD4+和CD8+细胞,从而诱导T细胞反应,并且由肽CH401和其他脂质链组成的共组装而成的疫苗具有更强的疫苗效力。在这篇综述中,以靶向纳米载体、癌症疫苗和抗癌药物的形式应用于治疗乳腺癌的肽类物是重点内容(图1)。未来,涉及肽类的抗癌策略将在临床转化方面有更多的应用。
图1来源:doi: 10.3389/fphar.2023.1052301
2、抗癌药物载体的多肽
核酸疗法是一种很有前景的癌症治疗策略,因为它具备克服诸多难题的能力,如:转移、耐药、基因变异、肿瘤微环境异质性以及肿瘤复发等。然而,小干扰RNA、micoRNA、适配体以及免疫佐剂核酸等的核酸疗法目前仍面临一些问题:溶解度低、稳定性差、渗透性弱、药物释放动力学不受控制以及缺乏靶向特异性障碍。
在这些靶向载体中,肽类物质因易于操作且具有天然的生物相容性而备受关注。除了良好的生物相容性以外,有理想序列的多肽还能进一步提高转染效率。
2.1针对乳腺癌的多肽
热休克蛋白gp96是一种位于癌细胞细胞膜上的分子伴侣,通常被用作癌症治疗的靶点。肽p37(LNVSRETLQQHKLLKVIRKKLVRKTLDMIKKIADDKY),能够特异性识别gp96的N端螺旋-环-螺旋序列,能够破坏分子内的螺旋-螺旋相互作用并抑制gp96的构象变化,从而破坏其伴侣功能。Liang等人用p37对阳离子脂质体CDO14进行修饰,形成具有针对gp96功能的p37-CDO14,并发现p37-CDO14能够特异性地与细胞膜上过表达的乳腺癌细胞中的gp96结合(图2)。
Pierschbacher和Ruoslahti从纤连蛋白中制备的三肽RGD能够识别多种整合素,这些整合素是由α和β亚基组成的某些糖蛋白,它们在癌细胞膜上过度表达,并参与血管生成、肿瘤生长和转移。Hazeri等人利用负载有AS1411适配体和肽RGDK-八精氨酸的介孔二氧化硅纳米颗粒制备了一种针对阿霉素(DOX)的靶向递送系统。结果表明,这种靶向递送系统在体内单剂量给药时能显著增强阿霉素的抗癌活性(图2)。
线性肽TT1(AKRGARSTA)常被用于修饰脂质体的表面,以实现对蛋白质p32的靶向作用,该蛋白质被称为跨膜gC1q受体,其在癌细胞和癌相关细胞(如活跃的血管生成内皮细胞、癌相关成纤维细胞以及癌相关巨噬细胞(TAMs)的细胞表面过度表达。细胞实验结果表明,用线性肽TT1改造的脂质体与三维乳腺癌球体的相互作用优于未改造的脂质体,并且总纳米囊泡中有50%被M2型人类原代巨噬细胞内化(图2)。
肽tLyP-1(CGNKRTR)是一种肿瘤导向配体,能够特异性地靶向在乳腺癌中过度表达的神经纤毛蛋白-1受体。Zhong等人发现,经过tLyP-1肽功能化改造的嵌合聚合体显示出良好的siNAC-1载体装载能力(高达14.4重量%),并显著抑制了MDA-MB-231细胞的侵袭和迁移。由Feng等人描述的肽CK3(CLKADKAKC)比其他乳腺肿瘤细胞(如4T-1、MCF-7和MDA-MB-435)对MDA-MB-231乳腺肿瘤细胞的结合能力更强(图2)。
线性十二肽p160(VPWMEPAYQRFL)对MCF-7和MDA-MB-435乳腺肿瘤细胞具有很强的结合力,这是基于其与角蛋白1受体的结合靶点得出的结论。其类似物肽p18(WXEAAYQRFL),在人体血清中具有蛋白水解稳定性,能与角蛋白1受体结合,而针对AU565细胞设计的载有DOX的P18-PEtOx-二油酰磷脂乙醇胺(DOPE)纳米脂质体所产生的抗肿瘤反应比自由DOX更强(图2)。
肽G3-C12(ANTPCGPYTHDCPVKR)能够与半乳糖蛋白-3受体特异性结合,该受体是一种30千道尔顿的蛋白质,与乳腺癌的转移和生长有关。该肽通过一个由肽GSG组成的连接子与1,4,7,10-四氮杂环十二烷-N,N',N"N‴-四乙酸(DOTA)连接,该连接子已用111In进行放射性标记以用于乳腺癌的靶向治疗。结果表明,肽G3-C12能够显著与人类MDA-MB-435(半乳糖蛋白-3)细胞结合(图2)。
雌激素受体(ERs)包含雌激素受体α(ERα)和雌激素受体β(ERβ)。其中,激活雌激素受体α(其在乳腺和子宫组织的增殖中起作用)在超过70%的乳腺癌中过度表达,并驱动乳腺组织增殖,是ERα阳性乳腺肿瘤的重要治疗靶点。Zhao等人报道的肽12a(HKIKHRLLQ)和13(Rcyclo(DILDap)RLLQ)与雌激素受体α有显著的结合(结合常数的值分别为118nM和85nM)(图2)。
在所有乳腺癌患者中,HER2阳性病例占比超过20%,这种类型的乳腺癌预后不佳,具有很强的侵袭性,并且复发率很高。因此,针对HER2阳性乳腺癌的靶向治疗药物对大多数处于疾病早期阶段的HER2阳性患者来说是有效的。Du等人设计了与聚乙二醇(PEG)结合的肽DH6(YLFFVFER)和RDH6(REFVFFLY),它们显示出良好的代谢稳定性和专门针对HER2阳性肿瘤的特性,而不会针对HER2阴性肿瘤。Stefanick等人报道了使用肽HERP5、HRAP、KAAYSL和AHNP这些针对HER2阳性肿瘤的靶向肽进行细胞摄取,其中肽KAAYSL的肿瘤摄取量最大。Kim等人制备了含有DOX-脂质偶联物和HER2pep(Stefanick等人所报道的肽序列:YCDGFYACYMDV)脂质偶联物的脂质体纳米颗粒,与非靶向纳米颗粒相比,0.5%肽密度的纳米颗粒下分别使HER2阳性肿瘤对EG8和EG18连接体的摄取量提高了约2.7倍和约3.4倍。A9非肽(WAVQNTDAV)通过特定位点与二乙烯基连接。使用三胺丙酸(DTPA)并用111In进行放射性标记来进行非侵入性HER2阳性肿瘤成像,结果表明DTPA-A9具有足够的体内稳定性。MartynaMichalska等人设计肽LTVSPWY功能化的合金CuInZnxS2+x量子点作为HER2阳性乳腺肿瘤的荧光纳米探针,肽LTVSPWY能够与HER2进行靶向结合。由Larimer和Deutscher选择的肽51(ATWLPVPVVGYFMASA)被用于靶向BT-474人类乳腺癌和其他HER2阳性癌症,以减少在其他组织中的非靶向积累(图2)。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是一种跨膜受体,是乳腺癌治疗策略的一个极具吸引力的靶点。其过度表达与乳腺癌患者的总体生存率降低、无病生存期缩短以及不良预后相关。Larimer等人从噬菌体微库中筛选出的肽1-D03(MEGPSKCCYSLALSH)对仅MDA-MB-435细胞具有高度特异性,且其作用机制与EGFR相关。肽GE11(YHWYGYTPQNVI)能够特异性地靶向EGFR并与EGFR的一个区域结合。Hailing等人合成了GE11改良的聚乳酸-羟基乙酸/D-生育酚聚乙二醇1000硫酸盐纳米颗粒,用于将沙林霉素递送至乳腺癌细胞中。结果表明,这些纳米颗粒显著增强了对过度表达EGFR的乳腺癌的治疗效果(图2)。
为治疗乳腺癌,研究人员设计了不同的肽序列,这些序列是根据癌症特异性表达的受体与之具有特定亲和力来确定的,目的是开发出一种能够靶向乳腺癌的理想肽。这些特异性表达的受体主要包括热休克蛋白gp96、整合素、gC1q受体、神经纤毛-1受体、角蛋白1受体、半乳糖凝集素-3受体、雌激素受体、HER2受体和表皮生长因子受体。这些靶向肽种类繁多,因此我们选择了其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肽在图2和表1中进行展示,例如靶向热休克蛋白gp96的肽p37、靶向整合素的肽RGD和RGDK-八个精氨酸、靶向gC1q受体的线性肽TT1、靶向神经纤毛-1受体的线性肽tLyP-1和CK3、靶向角蛋白1受体的线性肽p160和p18、靶向半乳糖凝集素-3受体的肽G3-C12、靶向雌激素受体的肽12a和13、靶向HER2的肽1-D03以及靶向EGFR的肽GE11。它们都与相应的受体具有高度的结合能力。此外,靶向肽类物质还存在诸多挑战,包括其在体内的稳定性问题、与目标组织的结合能力较弱、非目标组织的摄取量过高等等。低内化程度。
图2来源:doi: 10.3389/fphar.2023.1052301
表1来源:doi: 10.3389/fphar.2023.1052301
2.2用于抗癌药物载体的CPPs
细胞穿透肽(CPPs)与各类药物结合,通过直接渗透或内吞作用进入细胞膜,显著增强难渗透分子的抗癌效果,用于乳腺癌治疗。Nam等人开发了一种pH可激活的CPP二聚体LH2(单体序列:LHHLCHLLHHLCHLAG),利用肿瘤周围弱酸性微环境(pH≈6.0)将紫杉醇递送至三阴性乳腺癌细胞MDA-MB-231。Fan等人测试了穿膜肽CPPC(序列:GPGLWERQAREHSERKKRRRESECKAA)与乳腺肿瘤归巢肽SP90的偶联物(SP90-C)。该复合物对三阴性MDA-MB-231细胞展现出优异的靶向递送功能,可高效输送抗癌药物。Park等人通过将环形CPP(cCPP,CWRWRKWRWR)与靶向肽(TP1或TP2)及抗癌药物卡巴他赛(CBT)偶联,合成了针对乳腺肿瘤弱酸微环境(PH≈6.0)的智能递送系统。其中,TP1-cCPP-CBT偶联物在在MDA-MB-231(三阴性型)和MCF-7(激素受体阳性型)细胞中展现出显著抗增殖活性。研究采用5(6)-羧基荧光素(FAM)作为对照,通过共聚焦显微镜和细胞摄取实验验证TP1-cCPP或cCPP的靶向效率。BenDjemaa团队开发的穿膜肽gH625(序列:HGLASTLTRWAHYNALIRAFC)被用于构建CPP封装的隐形磁性siRNA纳米载体(CS-MSN),向三阴性乳腺癌MDA-MB-231细胞递送siRNA。该肽不仅促进siRNA胞内递送,还协助其从内涵体逃逸。团队进一步开发gH625与阳离子聚合物功能化的隐形荧光纳米颗粒(CS-FNP),优化后的纳米载体在MDA-MB-231细胞中的摄取率显著高于普通CS-FNP。pH响应肽GALA(序列:WEAALAEALAEALAEHLAEALAEALEALAA)在酸性环境下激活细胞膜相互作用,与肿瘤归巢线性五肽CREKA共同修饰氧化还原响应复合物,用于三阴性乳腺癌治疗。结果表明,该复合物具有优异转染效率,并能保护siRNA免受RNA酶降解。Wang等人利用肿瘤归巢肽tLyP-1(序列:CGNKRTR)通过神经纤毛蛋白-1(NRP-1)介导的CendR通路穿透细胞,修饰载药胶束共递送化疗药物与TRPA-1抑制剂,显著提升MDA-MB-231细胞的靶向治疗效果。主要穿膜肽总结见表2。
表2来源:doi: 10.3389/fphar.2023.1052301
三阴性乳腺癌(TNBC)细胞对化疗药物的内吞作用弱,治疗困难。细胞穿透肽(CPPs)可增强化学药物或siRNA对TNBC细胞的渗透。为提高内吞作用,我们选择了诸如肽二聚体LH2、肽C、cCPP、肽gH625、肽GALA和肽tLyP-1等许多CPPs来将化学药物或siRNA传递到TNBCs细胞中进行治疗。然而,CPPs在临床中的应用受限:1)CPPs的有效渗透浓度通常高于微摩尔,在体内由于CPPs的不稳定性难以发挥作用;2)缺乏选择性,通过静电/疏水作用渗透几乎所有细胞,导致脱靶效应。为克服此,研究转向设计靶向递送策略,如开发pH响应型CPP(靶向肿瘤微酸环境)或将CPP与靶向肽偶联,以提高肿瘤特异性并降低副作用。
3、基于肽的癌症疫苗
3.1基于肽的癌症疫苗正在进行临床试验
治疗性癌症疫苗处于当今医学发展的前沿。目前现有癌症疫苗主要包括:核酸疫苗(DNA/RNA疫苗)、蛋白质疫苗、灭活自体肿瘤细胞疫苗及纯化肿瘤抗原疫苗。截至2021年6月23日,乳腺癌领域共有44项治疗性癌症疫苗正在进行临床试验,其中:30项试验面向三阴性乳腺癌(TNBC)患者,21项试验招募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仅15项试验将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纳入入组标准。在这些临床试验中,肽疫苗在乳腺癌临床试验中占主导地位(20项,45.5%)。dePaulaPeres等综述乳腺癌中处于III期、II期、I/II期及I期临床试验的13类主要肽疫苗,包括:E75(KIFGSLAFL),GP2(IISAVVGIL),AE37(LRMKGVGSPYVSRLLGICL),P15(FLAEDALNTV),P14(NLMEQPIKV),P13(YLIELIDRV),P7(ILDDIGHGV),P5(ALMEQQHYV),P4(FLYDDNQRV),P3(KLDVGNAEV),MUC1-KLHconjugateplusQS-21(KLH-MBS-CVTSAPDTRPAPGSTAPPA-HGVTSAPDTRPA),MFP(PDTRPAPGSTA-PPAHGVTSA)andL-BLP25(STAPPAHGVTSAPDTRPAPGSTAPP)(表3)。此外,由于单肽疫苗免疫原性较差的主要原因,包括不同递送载体和佐剂的肽疫苗也被实施。
表2来源:doi: 10.3389/fphar.2023.1052301
3.2结合载体或佐剂的肽疫苗
Zamani等将长链多表位肽E75-AE36(序列:Ac-CGGGKIFGSLAFLAAAGVGSPYVSRLLGICL)与佐剂肽PADRE(序列:AKFVAAWTLKAAA)结合形成纳米脂质体疫苗,评估其对小鼠乳腺癌模型的免疫原性。结果显示,该疫苗显著提升干扰素-γ(IFN-γ)分泌及CD4⁺/CD8⁺T细胞应答。Zamani等(2022)进一步开发了由肽AE36(序列:Ac-CGGGVGSPYVSRLLGICL)和PADRE肽偶联单磷酰脂质A(MPL)佐剂构成的纳米脂质体疫苗。在TUBO乳腺癌小鼠模型中,该疫苗触发有效免疫应答,并诱导更强的Th1型免疫反应。Barati等将肽AE36与含DOPE(二油酰磷脂酰乙醇胺)、DOTAP(1,2-二油酰基-3-三甲基铵丙烷)及胆固醇的脂质体偶联,该配方可有效激活CD8⁺/CD4⁺T细胞应答。Zamani等探索了肽E75(序列:Ac-CGGGKIFGSLAFL)与多柔比星(DOX)的联合疗法,二者协同增强IFN-γ分泌及CD8⁺/CD4⁺T细胞反应。Wang等证实:在中国常用于治疗免疫缺陷的聚肌胞(PolyactinA,PAA)与肽E75联用,较单用E75显著提高CD8⁺/CD4⁺T淋巴细胞阳性率,并增强IFN-γ生成。含肽P5、MPL及PADRE佐剂的纳米脂质体疫苗在HER2阳性乳腺癌中展现显著抗癌效果,有效激活CD8⁺T细胞免疫应答。Talesh等将肽P5负载于由聚肌苷酸-聚胞苷酸[Poly(I:C)]和DOTAP-胆固醇组成的阳离子纳米脂质体,在体内外均诱导强效抗肿瘤反应。肽疫苗与载体/佐剂联用的作用机制见图3。
图3来源:doi: 10.3389/fphar.2023.1052301
3.3.新型肽疫苗
除将这些新型肽与载体和佐剂相结合(如表4所示)之外,还有许多新型肽被用作乳腺癌疫苗。Mahdavi等人报道,源自乳腺癌中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GF-1)受体的肽249(序列:GDLTNRCTMEEKPMEK)是一种潜在的乳腺癌肽疫苗候选物。该肽能强有力地结合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HC)Ⅱ类和Ⅰ类分子,并有效激活T细胞。此外,他们还合成了肽1412(序列:QPEQQETKKEEQ),该肽对多种测试的MHC亚型表现出优异的结合活性。研究采用肽E39(序列:EIWTHSYKV)与其免疫原性减弱的变体E39'(序列:EIWTFSTKV)进行联合免疫。免疫学分析表明,同时给予E39和E39'能够协同作用,诱导出功能最优的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CTL)群体。肽ErbB-2266-296(CGPSLLHCPALVTYNTDTFESMHNPEGRYTFGASCV)与天然的ErbB-2蛋白结合,通过模拟帕妥珠单抗来激活B细胞,并且卵清蛋白肽OVA323-339(ISQAVHAAHAEINEAGR)作为T细胞表位,它们被连接成一个脂质体系统,以诱导针对ErbB-2抗体的反应。小鼠实验证实,由肽ErbB-2266-296和OVA323-339激活的体液免疫应答提升7.3倍,并在体外诱导96%的肿瘤细胞死亡。Servín-Blanco等(2018)开发可变表位库(VEL)技术,筛选出长肽:45A2L(序列:AGDAEYXRAYLXGECVEXLRXYLXLGNXTLLRXDXPKAHVTYHPRS)、QA2L(序列:GPHXLRYFXTAVXWPGLVXPRFIXVGYVXDTQFV)及其野生型肽:PPE15L(序列:MDFGXLPPEXNSXRMYAGXGAXPMMAAXAAWNGLAXELGTXAASY)、PGRS(序列:LFXNGGAGGQGGXGGXGGXGGXGGXGMAXGPAGGTGGIGXIGGIG)(注:"X"代表20种天然氨基酸中的任意一种)。研究观察到,45A2L、QA2L、PPE15L与PGRS显著激活T细胞抑制肿瘤生长,并减少免疫小鼠肺部的转移灶。Ganneau等合成糖肽树状聚合物MAG-Tn3(含通用T细胞表位肽TT,序列:QYIKANSKFIGITEL),作为人用抗癌疫苗候选物。研究发现,MAG-Tn3诱导的Tn特异性抗体可高效杀伤人Tn阳性癌细胞,目前正针对乳腺癌患者进行I期临床试验评估。
表4来源:doi: 10.3389/fphar.2023.1052301
癌症疫苗需具备肿瘤特异性与良好耐受性,其已知优势超越化疗,因此基于肽的癌症疫苗在乳腺癌的预防与治疗中前景广阔。主要肽疫苗(如E75、GP2、AE37、P3、P4、P5、P7、P13、P14、P15、MUC1-KLH偶联物+QS-21、MFP及L-BLP25)已进入III期、II期、I/II期及I期临床试验。过去20年间,乳腺癌疫苗研究面临临床试验结果欠佳的挑战,主因在于单肽疫苗免疫原性较弱。然而,COVID-19疫苗接种运动推动技术革新为乳腺癌疫苗研发提供了新机遇。为引发持久的免疫反应,癌症疫苗可以与其他治疗方式相结合。与不同传递载体和佐剂连接的肽作为乳腺癌疫苗已得到广泛研究。传递载体正朝着不可降解和聚合纳米颗粒、病毒样颗粒和脂质纳米颗粒的方向发展,其中脂质体在提高细胞摄取以增强疫苗免疫原性以及帮助将肽基疫苗输送到淋巴结方面表现更优。肽基疫苗单药治疗主要针对癌前病变或(新)辅助治疗环境,而肽基疫苗与抗癌药物联合使用则用于晚期肿瘤。肽基乳腺癌疫苗显示出良好的前景,对癌症疫苗的进一步理解以及其制备和使用的技术进步都是重要的。
4、抗癌药物的多肽
4.1破坏细胞膜的肽
蜂毒肽中Melittin(GIGAVLKVLTTGLPALISWIKRKRQQ)约占蜂毒干重50%,通过破坏细胞膜在乳腺癌模型中展现显著抗癌活性。蜂毒肽作为抗癌剂的分子机制,Duffy等人证明,Melittin通过诱导乳腺癌细胞的细胞膜上无法进行EGFR和HER2磷酸化,从而导致癌细胞死亡,尤其是在三阴性乳腺癌和HER2阳性乳腺癌中。由于蜂毒素具有快速的裂解作用,因此以载体传递蜂蜂素是首选,Daniluk等人设计由纳米氧化石墨烯或纳米金刚石携带的蜂蜂素,并发现纳米氧化石墨烯载体可以增加蜂蜂素对乳腺癌的抗癌活性,纳米金刚石能够保护正常细胞免受蜂度毒素的破坏。蜂毒肽与经雌酮修饰的胶束复合物在胰蛋白酶消化作用下保持稳定,而与雌酮结合的胶束在对雌激素受体阳性MCF-7细胞的摄取量方面,相较于三阴性乳腺癌细胞系MDAMB-231显著增加6倍以上,并且具有较高的抗癌效果。为实现蜂毒肽与miR-34a的靶向协同递送,莫蒂埃等人合成一个由聚乙烯亚胺外壳(修饰有叶酸)、硫酸葡聚糖(作为配体)和接枝聚谷氨酸壳聚糖核心组成的纳米载体。结果表明,通过联合递送蜂毒肽和miR-34a,癌细胞的死亡明显增加54%。蜂毒肽用于治疗乳腺癌脑转移(BCBM),通过将CXCR4小分子拮抗剂AMD3100与聚(乳酸-β-氨基酯)纳米颗粒结合,并通过AMD3100纳米颗粒递送蜂毒肽,有效地抑制BCBM模型小鼠肿瘤的生长。此外,蜂毒肽具有良好的免疫调节活性,如增强Th1细胞功能。Liu等人制备了突变型白细胞介素-2(MIL-2),这是肿瘤免疫治疗中最为成功的细胞因子之一,并将蜂毒肽与之结合,形成了双功能融合蛋白-蜂毒肽-MIL-2。实验结果表明,蜂毒肽-MIL-2能够引发明显的抗肿瘤和免疫刺激效果。
4.2抑制转录因子活性的肽类物质
干扰肽(iPeps)即突变型转录因子变体,它们本身无活性,但能够通过紧密地“锁定”其结合伙伴来抑制转录程序。Beltran等人设计七种iPeps,包括iPep697Δ(KKKRKVAPAAVYCTRYSDR)、iPep697(KKKRKVWPAWVYCTRYSDR)、iPep682(KKKRKVPLVWPAWVYCTRYSDRPS)、iPep624(KKKRKVTDSQQPLVWPAWVYCTRYSDRPS)、iPep624W1ΔA(KKKRKVTDSQQPLVAPAWVYCTRYSDRPS)、iPep624W2ΔA(KKKRKVTDSQQPLVWPAAVYCTRYSDRPS)和iPep624ΔHEX(KKKRKVTDSQQPLVGAAGAGCTRYSDRPS)。这些干扰肽iPeps能够把靶向靶向Engrailed1(EN1)蛋白,主要因为它们的序列包含了来自同源域(HD)N末端的侧翼蛋白质序列以及构成EN1的特定六聚体结构。研究结果表明,iPep624和iPep682能迅速在过度表达EN1的乳腺癌细胞系SUM149PT中引发强烈的细胞凋亡反应。iPep697和iPep697Δ在2分钟内被细胞内化,并在40分钟后达到较高水平。Sorolla等人合成了活性的EN1-iPep(KKKRVPLVWPAWVYCTRYSDR)以及突变的EN1-iPep(KKKRVPLVAPAAVYCTRYSDR),并设计了包含四个肽RGD的两种iPep,包括RGD1(HGRGDLGRLKK)、RGD2(YTSGDQKTIKS)、RGD3(NLRGDLQVLAQ)以及RGD4(RGRRGDLATIHG)。EN1-RGD-iPep被用于对多西他赛纳米颗粒进行功能化,以促进肿瘤特异性靶向。结果表明,EN1-RGD-iPep降低了TNBC细胞的细胞活力,并诱导了细胞凋亡,且未显示出毒性,而EN1-RGD-iPep介导的多西他赛纳米颗粒通过整合素和静脉注射增加了肿瘤积累。他们还设计活性的EN1-iPep(KKKRKVPLVWPAWVYCTRYSDR)以及突变型的EN1-iPep(KKKRKVPLVAPAAVYCTRYSDR)。体外细胞毒性测试表明,EN1-iPep对人类基底样SUM149PT细胞具有高度的选择性毒性,而在MCF10A细胞(一种正常的乳腺上皮细胞系)中则没有这种毒性。此外,当通过聚(丙烯酸)修饰的聚(丙烯酰胺甲基丙烯酸酯)纳米颗粒共同递送时,EN1-iPep能够通过协同的药理作用增强多西他赛诱导细胞凋亡的功能。
4.3治疗耐药性乳腺癌的多肽
抗癌药物耐药性是限制化疗在乳腺癌治疗中广泛应用的关键问题。对于许多患者,尽管接受了内分泌治疗,肿瘤复发和转移仍难以避免。耐药机制主要包括两大类:固有耐药性(肿瘤在化疗前即存在的先天抗性)和获得性耐药性(在化疗药物作用下逐渐产生)。其中,获得性耐药性问题更为复杂,因其难以预测且常伴随 多药耐药性(MDR) ,即肿瘤同时对多种结构及作用机制不同的化疗药物产生抵抗。导致耐药的因素众多,主要包括:ABC转运蛋白过度表达(导致药物外排)、药物失活、药物靶点改变、细胞凋亡通路失调、肿瘤干细胞(CSCs)的存在以及 上皮-间质转化(EMT)。
在耐药性乳腺癌中,药物外排机制主要由ABC转运蛋白家族介导,其中P-糖蛋白(P-gp)是典型的代表。P-gp作为能量依赖性的药物外排泵,可主动外排多种结构各异的抗癌药物转运至细胞外,导致细胞内药物浓度显著降低,无法达到有效治疗水平。为克服耐药性,阻断P-gp转运功能成为关键策略,主要依赖特异性特异性抑制剂或结构改造技术。第一,肽-药物偶联物的增效机制。Mozaffari等人通过戊二酸连接子(非裂解型)和二硫键连接子(还原敏感型)分别合成共轭物[R5K]W7A-DOX和[R5K]W7C-S-S-DOX。这该设计融合有DOX和[R5K]W7A含线性W7A及环状R5K结构域)。实验显示:[R5K]W7A-DOX对耐药细胞MDA-MB-231R的活性比游离DOX高16倍,其作用机制可能通过分子结构修饰规避P-gp识别。细胞毒性分析表明,5μM[R5K]W7A-DOX对心肌及肾细胞无明显损伤,而同等剂量游离DOX在72小时内可诱导显著凋亡及形态破坏,印证其安全性优势。第二,纳米载体延长胞内滞留的策略。Zhang等人设计依托泊苷共价结合肽Nap-GFFpYK,显著提升药物水溶性及胞内滞留能力。该结合物对过表达MDR1(P-gp编码基因)的耐药细胞抑制活性提升20倍,证实延长胞内滞留可削弱P-gp外排效应。进一步,Zhi等开发酶响应型纳米系统AuNRs-LAX。核心组分LAX由溶酶体蛋白酶CathepsinB底物四肽(GFLG)、依托泊苷及脂酸构成,可在肿瘤溶酶体内特异性释放药物。金纳米棒载体(AuNRs)尺寸(>100nm)远超P-gp底物结合腔(约5-10nm),通过物理空间位阻阻断P-gp介导的外排。实验结果显示,AuNRs-LAX使MCF-7/ADR细胞的耐药指数从955.0降至1.7,近乎完全逆转耐药性。第三,PKC磷酸化调控的抑制途径。P-gp连接区(linkerregion)的磷酸化修饰可增强其外排活性,而蛋白激酶C(PKC)家族是介导该过程的关键激酶。为抑制此通路研究者合成PKC假底肽P1-P7(如P1:NmFARKGALRQ、P2:FARKGALRQ、P3:NmRFARKGALRQKNV、P4:RFARKGALRQKNV、P5:NmRKRTLRRL、P6:RKRTLRRL、P7:NmNDSRSSLIRKR),其中P1通过竞争性抑制PKC与P-gp的结合,有效阻断磷酸化过程。机制研究表明,P1可显著下调P-gp的ATP酶活性,减少药物外排,为逆转MDR提供新靶点。
除药物外排机制外,细胞凋亡失调也是乳腺癌耐药性的关键因素之一。其中,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信号通路,特别是其下游关键效应分子——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ERK)的异常持续激活,是驱动凋亡失调的核心机制。ERK通过磷酸化下游转录因子,激活一系列促进细胞存活和增殖的基因表达,从而抑制细胞凋亡程序。在此背景下,Sheng等人开发一种靶向递送策略:利用硫酯连接子(GGCG)将转铁蛋白受体靶向肽T10(HAIYPRH)与ERK抑制肽(MPKKKPTPIQLNP)共价连接构建出双功能嵌合肽T10-ERK(HAIYPRHGGCGMPKKKPTPIQLNP)。该嵌合肽被设计用于与阿霉素(DOX)联用,逆转乳腺癌耐药性。研究结果表明,T10-ERK通过阻断ERK生存信号通路,有效克服耐药细胞对凋亡的抵抗,从而与DOX产生协同效应,显著降低耐药性并增强药物疗效。为逆转乳腺癌细胞凋亡失调,激活溶酶体凋亡途径是有效策略之一。其中,酶响应型四肽GFLG因对肿瘤溶酶体中过度表达的组织蛋白酶B的高度敏感性,被广泛应用于药物递送系统设计。例如,通过GFLG连接mPEG化树状聚合物与阿霉素(DOX),可形成自组装复合物DOX-GFLG-mPEG。该复合物经内吞进入肿瘤细胞后,在溶酶体内被组织蛋白酶B特异性切割,释放DOX并触发溶酶体膜透化进而通过组织蛋白酶-Bid-线粒体轴激活Caspase依赖性凋亡,显著增强溶酶体介导的细胞死亡效应。另一方面,增殖细胞核抗原(PCNA)作为DNA代谢的核心支架蛋白,其功能涵盖:细胞周期调控、DNA复制与修复、染色质重塑、蛋白质降解协调及DNA甲基化维持。与癌症相关的PCNA(caPCNA)在结合域上有一个8个氨基酸的肽caPeptide(CLGIPEQEY)。Lingeman等人利用四环素诱导系统在顺铂耐药MDA-MB-231细胞中上调caPeptide的内源性表达。结果表明,caPeptide+顺铂联合处理使细胞凋亡率提升3.2倍,机制为抑制跨损伤合成(TLS)修复+增强顺铂诱导的DNA双链断裂累积。Ras相关核蛋白(Ran)通过促进修复蛋白的核输入(RanGTP)和介导损伤RNA/DNA的核输出(RanGDP)循环调控核运输。当Ran浓度达到阈值时,肿瘤细胞中的DNA损伤得以成功修复。Haggag等人设计Ran鸟苷酸交换因子(RCC1)抑制肽(RAN-IP,其序列为CAQPEGQVQFK)。该肽通过特异性阻断MDA-MB-231乳腺癌细胞中Ran-RCC1蛋白相互作用,有效抑制RanGTP生成。为提升递送效率,研究团队采用薄膜水化法制备脂质体,实现RAN-IP和DOX的共装载。在荷瘤小鼠模型中,该共递送系统有效逆转多耐药活性,并显著增强肿瘤对Doxde敏感性。
克服乳腺癌耐药性的有效策略之一是靶向新受体以规避耐药通路。四分支肽通过其分支结构(该结构包含人类神经肽素(NT4,序列为(ELYENKPRRPYIL))与膜表面硫酸软骨素蛋白聚糖(CSPG)或低密度脂蛋白受体(LDLR)家族的硫酸化糖胺聚糖链或不同的内吞受体相结合,该靶点结合特性源于其分支构型。研究将其与甲氨蝶呤(MTX)偶联用于MTX耐药乳腺癌治疗。结果表明,NT4-MTX偶联物可有效规避耐药机制,并被耐药乳腺癌细胞高效内化。Brunetti等人基于hY1R靶向肽[F7,P34]-NPY(YPSKPDFPGEDAPAEDLARYYSALRHYINLITRPRY)的结构,在其第4位和第22位赖氨酸引入修饰,构建新型双修饰肽。该修饰肽与甲氨蝶呤(MTX)的偶联物通过hY1R介导的内化作用,显著增强了对MTX耐药乳腺癌细胞的杀伤效果,疗效优于游离MTX。在ERα阳性乳腺癌的内分泌治疗中,耐药性是关键临床障碍。机制研究表明,抑癌蛋白PHB2通过直接结合核ERα抑制其转录活性。而乳腺癌特异性蛋白BIG3通过胞质滞留PHB2,解除其对ERα的抑制作用,导致ERα信号通路的构成性激活。Yoshimaru等人合成了一个名为ERAP(11R-GGG-QMLSDLTLQLRQR)的负性肽,它能够将PHB2从BIG3中释放出来,肽ERAP的治疗能够增强ERa阳性乳腺癌细胞对他莫昔芬的反应性。附着素1(Anxa1)是一种明显在肿瘤血管内皮细胞表面表达的生物标志物。在nullAnxa1的小鼠中,血管生成的缺失显著抑制了肿瘤的生长。A名为IF7(IFLLWQR)的肽能够以高亲和力和高特异性与Anxa1结合,因此Yu等人通过将肽IF7与紫杉醇偶联,合成了IF7-PTX-NP这种纳米递药系统。实验结果表明,IF7-PTX-NP能够显著诱导肿瘤组织坏死以及肿瘤血管内皮细胞凋亡,且对小鼠无明显毒性。
4.4其他抗癌肽
长链非编码RNA(lncRNAs)是长度超过200个核苷酸的非编码转录本,可调控肿瘤细胞增殖与侵袭。LINC00908在TNBC中显著下调(与非TNBC及正常组织相比),其开放阅读框编码一个60个氨基酸的肽段ASRPS(MTTKMRRLRPSAPSGLGQEQEAEVVEGCFPAVTETPFAPAYIKKRGGRIWSSDPRSDGEH)。肽通过卷曲螺旋结构域(CCD)直接结合STAT3,抑制STAT3第705位酪氨酸(Y705)的磷酸化,导致VEGF转录活性与蛋白表达下调,最终显著降低TNBC的微血管密度(血管生成抑制的核心表型)。肽AFPeq(环化结构:cyclo(EKTOVNOGN),其中O为羟脯氨酸),由Jacobson等人开发,通过头-尾环化模拟α-胎蛋白(AFP)的抗乳腺癌位点。该肽在MCF-7乳腺癌异种移植模型中:0-7天显著抑制肿瘤生长,7-14天完全阻滞肿瘤进展,对肝脏和肝细胞癌细胞系无毒性作用。此外,AFPeq在小鼠、大鼠、狗和猴子中具有良好的耐受性。目前临床应用有两种专门用于治疗乳腺癌的肽,分别是帕西瑞特和戈塞林。Pasireotide(图4A,环化(Hyp(未知)-Phg-WKY(Bn)F))可以特异性结合生长抑素受体亚型sst5和sst1、2、3,并显著抑制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IGF-1和生长激素的分泌。Goserelin(图4B,XHWSYSLRP)表现出不同的作用机制。它可以作为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GnRH)激动剂结合前脑垂体叶受体。通过低蛋白水解敏感性的方式模拟GnRH,并刺激垂体前叶分泌黄体生成素(LH)和促卵泡激素(FSH)。
图4来源:doi: 10.3389/fphar.2023.1052301
肽类抗肿瘤药物的开发受限于序列设计、结构修饰和药理筛选等关键因素。截至2022年5月,全球共有118种肽类药物获批临床(7种诊断试剂),但仅占所有新药的2%,随着基因技术、信息技术和基因组学技术的进步,肽类药物的研究已进入医学发展前沿。表5列举的新型抗肿瘤肽通过差异化机制设计抑制肿瘤生长(图5)。肽类药物的抗肿瘤机制大致包括:①递送系统优化:研究人员选择纳米载体来传递蜂毒肽和其他抗癌药物(肽类、化疗药物或siRNA),用于乳腺癌治疗。结果表明,蜂毒肽具有明显的抗癌活性。②转录因子抑制:部分肽类药物通过紧密地将转录因子的结合伙伴“隔离”起来,阻断形成活性变构体,抑制促癌转录程序。③多药耐药性(MDR)的逆转:MDR是导致90%以上癌症死亡的重要原因,机制涉及:ABC转运蛋白过表达、药物靶点修饰、凋亡失调等。为应对这些问题,研究者设计富含精氨酸/色氨酸的肽类药物可逆转或规避外排的作用,此外这些肽还可以通过激活溶酶体凋亡途径或抑制生存信号,来对抗凋亡失调。临床药物研究证明,肽-药物偶联疗效显著由于单独使用药物。④新型靶向策略:研究者设计一些肽可特异性结合新靶点的肽类分子,以克服多药耐药性并规避耐药机制。结合新的靶点的方法来治疗多药耐药性,并绕过耐药机制。还有一些新型肽通过差异化作用抑制乳腺癌治疗,例如下调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表达或模拟α-胎蛋白(AFP)的抗乳腺癌活性。
图5来源:doi: 10.3389/fphar.2023.1052301
表5来源:doi: 10.3389/fphar.2023.1052301
5、总结与未来战展望
肽类物质参与并调节着生物体内各种系统、器官、组织和细胞的功能活动。它们在生命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肽类的抗癌药物的研究因其可大规模生产、安全性良好以及适应性强等特点而备受关注。在乳腺癌的临床治疗中,肽类已被用作有前景的靶向载体、抗癌疫苗和抗癌药物。先前的研究表明,肽类能够特异性地与乳腺肿瘤细胞的不同靶点结合。在这篇综述中,我们总结了乳腺肿瘤细胞的九个靶点,包括HSPgp96、integrins、gC1qreceptor、neuropilin-1receptor、keratin1receptor、galectin-3receptor、ERs、HER2andEGFR.。针对各靶点,已开发特异性多肽配体介导抗癌药物精准递送。此外,能够通过静电和疏水相互作用穿透细胞膜的CPPs也被用于将抗癌药物递送至乳腺癌细胞中。尽管CPPs无法区分肿瘤细胞与正常细胞,因此有必要将CPPs与靶向部分结合。基于肽的疫苗是癌症治疗疫苗开发领域的前沿药物之一。一些针对乳腺癌的肽疫苗现已在III期、II期、I/II期和I期临床试验中进行研究,包括肽E75、GP2、AE37、P3、P4、P5、P7、P13、P14、P15、MUC1-KLH结合物加上QS-21、MFP和L-BLP25。由于单肽疫苗的免疫原性较差,因此设计了一些与载体或佐剂相结合的基于肽的疫苗。具有细胞毒性的多肽可通过多种机制诱导肿瘤细胞凋亡(如蜂毒肽破坏细胞膜、iPeps抑制转录)。更重要的是,特定多肽能逆转多药耐药性(MDR)——这是乳腺癌死亡的重要诱因。其作用机制包括:逆转药物外排泵功能、调节凋亡通路或旁路耐药信号传导。
2000年之后,人们发现或设计出多种用于治疗乳腺癌的肽类物质。然而,在乳腺癌的临床治疗中,新肽类药物却很少被采用。截至2022年5月,仅有两种抗癌肽——帕西瑞特和戈塞林——被批准用于治疗乳腺癌。肽类药物临床应用受多种因素的限制,包括靶点选择、序列设计、结构修饰、高蛋白水解敏感性以及临床前研究等。首先,抗癌肽对乳腺癌的靶向治疗效果较弱,主要是因为癌细胞靶点受多基因调控网络和旁路信号通路的影响,抗癌肽不能通过结合单一的癌细胞靶点来安全有效治疗乳腺癌。因此,开发和研究具有协同机制或能针对多个点的多功能肽来提高治疗效率。其次,肽的序列设计限制新型肽类药物的开发。肽的序列需要不断改进,以获得适用于高效乳腺癌治疗的肽。例如,需要替换不稳定氨基酸残基以避免肽在体内发生异构化、糖基化和氧化反应。同时,还需要优化肽的物理化学性质,如分布、等离子点和pH值等。仅仅依靠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技术来设计基于肽的药物而不考虑其使用的相关因素是不够的。因此,新的抗癌肽的序列通常源自具有抗癌活性的天然肽;例如,来自蛇毒或蜂毒以及体内的活性肽。此外,由于肽具有较高的蛋白水解敏感性、较高的非靶组织摄取率和较低的体内内化率,因此常常需要对肽进行结构修饰。为了克服这些内在缺点,已经采取了许多策略。肽的链状结构通常具有高弹性;因此,设计了具有一个环或两个环的稳定环状肽。肽类物质还被与药物、抗体或寡核苷酸相结合,用于靶向治疗,且副作用极低。此外,还可设计经过聚乙二醇、糖基化、脂质体或佐剂修饰的口服肽,以避免在体内被蛋白酶降解,从而提高生物利用度。最后,必须考虑诸如药理学、毒理学和代谢学等预临床研究,这些是临床试验的必要前提。这些预临床研究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以确保基于抗癌肽的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新肽类药物的成功研发最终需要投入大量的研究、时间和资金,但作为回报,新肽类药物所带来的收益预计将会非常巨大。用于乳腺癌治疗的肽类药物或疫苗在未来的应用中具有很大的潜力,并有望成为未来制药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Li L, Duns GJ, Dessie W, Cao Z, Ji X and Luo X (2023), Recent advances in peptide-based therapeutic strategies for breast cancer treatment. Front. Pharmacol. 14:1052301. doi: 10.3389/fphar.2023.1052301
免责声明:
本文为行业学术交流用途,所涉文献解读及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学术理解,不作为任何机构或领域的权威结论。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可联系删除。
Cell: +86-158-2124-5079
Email: joseph@namicrobio.com
NAMICROBIO Co., Ltd
发布于:陕西省股市配资技巧,配资门户难简配资,中国十大杠杆配资公司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 上一篇:杭州配资这就需要加强宣传和引导
- 下一篇:怎么办理加杠杆炒股